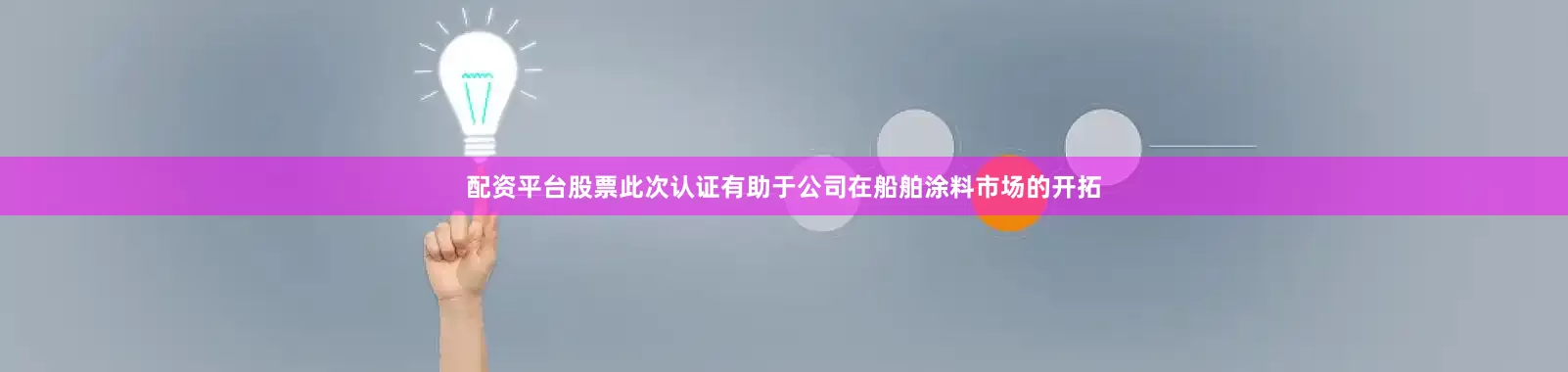“你这个小流氓!怎么会是你!” 一声尖锐至极的惊叫,宛如一道凌厉无比的闪电,在刹那间毫不留情地划破了屋内原本那如死水般宁静的氛围。这喊声太过突兀,我被惊得像是遭了电击一般,猛地抬起头来。只见对面伫立着的那位中年妇女,双眼瞪得犹如铜铃,满满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,五官因极度震惊而有些扭曲。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,像是秋风中的残叶,伸出的手指直直地指向我,那指头止不住地微微哆嗦,仿佛在宣泄着她此刻内心无法抑制的激动情绪。在她身旁,正是今日与我相亲的姑娘,此刻也是一脸受到惊吓的模样,眼神里尽是茫然失措。她先是慌乱地望向自己的母亲,那眼神中带着一丝无助的求救;随后又将目光匆匆投向我,一脸的不知所措,仿佛在努力探寻这突然变故背后的原因。
在那一刻,我整个人完全懵掉了,脑袋里一片混沌,犹如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,全然不知该如何应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状况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我们明明是初次见面,怎么刚一照面,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她口中的 “小流氓” ?一旁的介绍人也被这毫无预兆的一幕惊得呆立在原地,脸上原本挂着的那抹笑容瞬间僵住,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了。很显然,这样令人惊愕不已的开场,是谁都未曾预料到的。
展开剩余84%一股犹如汹涌潮水般的情绪,夹杂着被当众羞辱的怒火以及满心的莫名委屈,“轰” 地一下涌上了我的心头。然而,即便内心翻江倒海,我还是强忍着愤懑,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,开始在记忆的深处努力地搜寻,试图找到任何与眼前这位妇女有关联的蛛丝马迹。
我的父亲是一位手艺精湛绝伦的木匠,一年到头都被繁重的活儿缠身,不是在东家家中专注地干活,就是在去往西家的路途上奔波,平日里很难得在家里看到他的身影。
在我十五岁那年,麦收刚刚结束,大地还残留着丰收后的余温。父亲又和往常一样,背着他那装满各种工具的陈旧工具箱外出干活去了。虽说那时我年纪尚小,但个头却早早超过了父亲。父亲这一走,家里那些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农活,便自然而然地全都压在了我和母亲单薄的肩头上。
记得那天,天边刚泛起一丝微弱的曙光,四周依旧沉浸在一片静谧的黑暗之中,我便跟随着母亲扛着镢头,脚步匆匆地朝着农田走去。初夏的田野带着丝丝凉意,仿佛还未从沉睡中完全苏醒,田间的露水悄无声息地打湿了我们的裤脚,冰冷的感觉顺着腿部蔓延开来。我心里憋着一股强烈的劲儿,一心想着要在母亲面前好好表现,让她知道我已然长大成人,可以为家里分担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了。
然而,现实却给了我重重一击。刚挥动几下镢头,我咬紧牙关,竭尽全力地往下使力,只听见 “咔嚓” 一声异常清脆的声响,手中握着的镢头把竟然应声而断。断裂的木茬子尖锐无比,瞬间刺得我的手生疼,钻心的疼痛让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
母亲听到动静,直起弯着的身子,转过头来望向我。看到我手中断成两截的镢头把,她无奈地叹了口气,话语中夹杂着一丝责备:“早都跟你说别逞强,你就是不听!这下可好,镢头把断了,这农活还怎么继续干下去?依我看,你还是赶紧回家去温书吧,要是能考个好大学,将来有了出息,也能让我们脸上增添光彩。”
母亲一直对我寄予厚望,盼望着我能像邻村那些优秀的孩子一样,在高考中脱颖而出,顺利跳出农门,改变一家人的命运。但我心里十分清楚,对于书本上那一堆枯燥乏味、晦涩难懂的知识,我实在是提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,学习成绩也一直处在班级的末尾位置。别说是考上那些令人向往的好大学,就算是考个普通的大专院校,对我而言也是困难重重,犹如攀登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。
家里人越是想方设法地给我腾出复习的时间,我内心的抵触情绪就越发强烈。相较于对着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书本,我宁愿在田间尽情挥洒汗水,辛勤地劳作,感受泥土的芬芳和劳动的充实。
我满心沮丧地拎着断了把的镢头回到家中。屋内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,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我翻开课本,才看了没两行字,上下眼皮就开始不听使唤地不停地打架,困意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涌来。实在是坐不住了,我索性把课本一推,站起身来,在狭小的院子里烦躁地来回踱步。不经意间,目光落在那断掉的镢头把上,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:何不去后山砍根合适的树枝,自己动手安装一个新的镢头把呢?
小时候,父亲做木工活时,我常常在一旁看得入迷,那些看似简单的小活计,像安装镰刀把、镢头把之类的,我自认为还是有一定把握能够做好的。想到这儿,我心里顿时涌起一阵兴奋,仿佛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,可以暂时摆脱那令人头疼不已的书本。我迫不及待地找出家里的斧子,兴致勃勃地往后山奔去。
后山有一片坡地,名义上是归生产队所有。这片坡地上长满了密密麻麻、高低错落的树木,一片郁郁葱葱的生机勃勃之景。这一切都多亏了村里的一个老光棍,他性格极为孤僻,常年独自一人住在山脚下那间破旧不堪的小屋里。他把守护这片林子当作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,谁要是胆敢在山上动一草一木,他绝对会不顾一切地拼命阻止,绝不留情。
我上山的时候,特意留了个心眼,远远瞧见他正躬着腰在自家门前的麦地里割麦子。看到这一幕,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,觉得这下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动手砍树了。
我在林子里来回转了一会儿,很快便相中了一棵粗细恰好合适的小树。我往手心吐了口唾沫,用力搓了搓,试图让手变得更加有力。随后高高举起斧子,鼓足全身的力气,带着十足的决心,就要朝着树干砍下去。
却万万没有想到,我的斧头还没碰到树干,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如炸雷般的断喝:“好大的胆子!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跑到山上砍树,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!把斧子给我放下,跟我去大队部走一趟!”
这声音尖锐刺耳,如同敲响的警钟,我一听就知道,肯定是那个看山的老光棍!他的嗓门大得惊人,在村里向来是出了名的不讲情面,村里人对他都忌惮三分。前些日子,他亲二叔悄悄上山想砍棵小树回去当柴火,结果当场就被他给逮个正着。他二话不说,直接夺下二叔手中的斧子,硬生生把人连带着斧子一起送到了大队部。
后来,他二叔不仅要在村小学门口的墙上张贴检讨书,还被罚款五十块钱。这事儿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,所有人都清楚这老光棍是个不好惹的主儿,谁要是招惹了他,准没好果子吃。
当时,我被吓得魂飞魄散,心脏仿佛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,哪还敢有丝毫的停留。抓起斧子,转身就一头扎进林子深处。身后,那老光棍的叫骂声和追赶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每一声都像是一道道无情的催命符,紧紧地缠上我。我慌不择路,只顾着在错综复杂的树丛中疯狂地穿梭,树枝无情地剐蹭在脸上,疼得我龇牙咧嘴,但此刻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,只想尽快摆脱这可怕的追赶。
眼见着他离我越来越近,那张爬满深深皱纹、写满愤怒的脸仿佛就在我的脖颈后面紧紧跟着。我心里一着急,脚下没注意,一不小心踩在了一块松动的石头上。
刹那间,只觉脚底猛地一滑,脚下的那块石头 “咕噜噜” 带着一股势不可挡的劲儿,沿着陡峭得近乎垂直的山坡,如离弦之箭般急速滚落。与此同时,我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,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狠狠拽住,身不由己地朝着山坡下方疯狂翻滚而去。
在这混乱不堪的瞬间,我的脑海中宛如被一片浓重的迷雾彻底笼罩,完全陷入了一片空白的状态。耳边,狂风在肆无忌惮地呼啸着,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咆哮,而我的惊叫声也夹杂其中,那声音因为极度的惊慌失措,早已变得不成腔调,尖锐且绝望。
说来也是幸运,这片山坡尽管地势陡峭得让人胆寒,却并没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悬崖峭壁存在,再者,地面上长满了茂密且湿滑的蒿草。这些蒿草宛如一层天然的柔软护垫,在我滚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缓冲作用。倘若没有这两个幸运因素,我这条小命恐怕当场就要葬送在这荒无人烟的野外了。
就这样,我如同一个完全失控的皮球,一路 “骨碌碌” 地疯狂翻滚,径直滚到了山脚下。这一番折腾,让我摔得浑身酸痛、七荤八素,眼前金星直冒,脑袋也像是要炸开了一般疼痛难忍。
好不容易,身体终于停了下来。我强忍着不适,晃了晃昏昏沉沉的脑袋。刚刚庆幸自己总算是摆脱了那个老光棍的穷追不舍,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粗气,突然,就感觉自己一头撞上了一个软绵绵、热乎乎的不明物体。
这突如其来的碰撞吓得我下意识地发出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惊叫,我手忙脚乱、跌跌撞撞地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。当我定睛一看,眼前所呈现的场景,瞬间把我惊得下巴都差点脱臼,与刚才被追赶时的惊慌相比,此刻的我简直陷入了一种更加不知所措的绝境。
原来,我撞上的竟是一位正蹲在草丛里如厕的中年妇女!很明显,她当时正在进行这件极为私密的事情,裤子都褪到了膝盖的位置。而我这毫无预兆、犹如噩梦般的一撞,让她整个人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上。此刻,她的脸上满满都是惊恐与羞愤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神情,那表情仿佛是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,令人不忍直视。
在那一刻,我的脸 “唰” 地一下就红到了耳根,滚烫的热度好似要把我的脸皮灼伤,羞耻与尴尬的情绪如汹涌的潮水般将我彻底淹没,我恨不得立刻能找到一个地缝,直接钻进去,永远躲开这难堪的一幕。我满心愧疚,磕磕巴巴、语无伦次地连声道歉:“对…… 对…… 对不起,大娘,我……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,实在是…… ” 说着,大脑在一片混乱中,我下意识地就想伸出手去拉她一把,希望能稍微弥补一下自己所犯下的这个弥天大错。
发布于:云南省配资业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